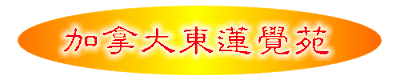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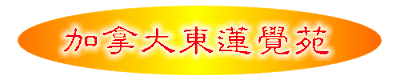
![]()
|
神秀惠能偈頌辨解 李潤生 (續六月刊) 身是菩提樹,心如明鏡臺, 時時勤拂拭,莫使有塵埃。 -神秀-
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非臺; 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! -惠能- 丁、 次頌解疑 針對神秀所撰偈文,惠能所回應的,依今所流行的宗寶本《六祖壇經》及《景德傳燈錄》、《五燈會元》等禪典所錄,唯有「菩提本無樹」那一偈頌,別無其餘,不過依較早的敦煌本《六祖壇經》所載,還有「心是菩提樹,身為明鏡臺,明鏡本清淨,何處染塵埃」那次頌的撰作,不過學者多疑此偈為前偈的「衍文」如國內禪宗學者郭朋,在其所撰著的《壇經導讀》及《壇經校釋》中,都有註文加以評論言:「『心是菩提樹,… 何處染塵埃』這一偈頌,當屬衍文,尤其是前兩句,當異是重復神秀的話,更非惠能思想。」愚見以為郭朋先生在沒有對慧能與神秀彼二偈作審細分析前,便輕率地作出這個案語,實在不敢苟同。我們不妨分三小節來加考察:其一、次偈是否為前偈的衍文?其二、次偈的前二句是否重復了神秀的話?其三、前二句是否非慧能思想? 一、次偈非衍文:惠能「菩提本無樹」那前偈,重點在蕩相顯智,在文詞上較重於破:「心是菩提樹」這次偈、重點在安立法相以顯用,在文詞上較重於立。破則以般若無分別根本智悟入本原佛性,故即相而離相,無一法得立,因此於頌中把一切「菩提樹」、「明鏡臺」諸名相盡皆遮遣,所謂「菩提樹本無樹、明鏡亦非臺」便是,至於「佛性」本亦離言,實不可分別,不可得說,方便言之姑且名之為「清淨」,所以言「佛性常清淨」,順著這種遮破的思路,到了宗寶本的《壇經》,便更徹底地把「佛性常清淨」修訂為「本來無一切」(按:「無一物」應解作「無有一一實性實相的自性實物存在」。而非謂「空無所有」)。這樣便更能彰顯般若無相之言。如是,以「般若正智」證入本原佛性,無一法得立,故亦無「塵埃」煩惱之相(按:般若智起,則煩惱當必降伏,其體用既無,其性相亦當不起),故偈言「何處有塵埃」。至於「心是菩提樹」這次偈,重點在安立法相,以顯修證的大用,所以運用般若後得智,有分別地說明悟入「佛性」前的修行境界,故前半偈言: 「心是菩提樹,身為明鏡臺」。又正顯般若智證入「佛性」時為「清淨無染」境界,故後半偈言:「明鏡心地本清淨,何處染塵埃。」以有所立故,因而有樹、有臺、有明鏡、有塵埃、作出種種譬喻,以顯般若的修證大用,并藉此以糾正神秀偈喻的失當。由此分析,當知惠能前後二偈,各有體用,各有旨趣,不宜妄指後偈為前偈的「衍文」。 二.非神秀偈文的重復:神秀偈文首句言「身是菩提樹」,惠能則言「心是菩提樹」。就形式上言,神秀與惠能俱用「暗喻語句」,但依內容而說,則兩相異趣,故「心是菩提樹」實非「身是菩提樹」的「重復」,而是糾正神秀所言「身是菩提樹」的失誤。何則?所言「身是菩提樹」實不應理故。以「菩提」是「大覺」義,這是淨化的「識心」活動,非關於「色身」。修養「色身」雖然可以影響「識心」,但究竟不能說「色身」是「菩提大覺」的因,所以把「菩提樹」以比喻「色身」實有點不倫,固不善巧,亦不通達。今惠能改以「菩提樹」暗喻「識心」,則足以顯示:欲得「菩提大覺」,必須修養其「心」,故《壇經》云:「般若無形相… 迷人口念,智者心行;不修即凡,一念修行,法身等佛。」所言「修心」,就是修般若行,是成就「菩提佛果」的正因。故知「修心」譬如扶植「菩提之樹」,使其能開花結實.所以惠能偈言「心如菩提樹」.實契正理,糾神秀失,誠非神秀偈文的「重復」可知。 又惠能次句「身為明鏡臺」,亦非重復神秀「心如明鏡臺」而成,反而應是糾正「心如明鏡臺」的失誤而撰作。何則?在形式言,「心如明鏡臺」是「明喻」;而「身為明鏡臺」則是「暗喻」。在內容言,前者的主體是「識心」,後者的主體卻是「色身」。神秀以「明鏡臺」比喻「識心」實不應理,因為「明鏡臺」一詞是「偏正結構」,以「明鏡」來修飾「臺」,意指「明鏡之臺」。「明鏡」屬偏,屬賓位,「臺」屬正,屬主位。因此「明鏡臺」的主體是物質性的「臺架」,依此「臺架」才可以把「明鏡」鑲嵌上去。我們可以喻「識心」為「明鏡」,因為彼此都有「能照」作用;但以「明鏡之臺架」以比喻「識心」則不大妥當,因為「臺架」共許是「明鏡」之所依處,但不許有「能照」作用,而「識心」則必有「能照」之用。若言「明鏡臺」只有「明鏡」義,沒有「臺架」義,故可比喻「識心」,則「臺」義懸空,徒增葛藤,失卻詩趣,終不如惠能「身為明鏡臺」說來合理。因為「明鏡臺」是「明鏡」之所依處,猶「色身」是「扶根塵」,是「識心」之所依處。「明鏡」與「識心」都具「能照」作用,故可以「明鏡」以喻「識心」;「明鏡臺」與「色身(根身)」,皆無「能照」作用,但俱有「能照體之所依託」義─「明鏡」依「臺」而「能照」;「識心」依「色身(根身)」而「能照」─所以運用「明鏡臺」以喻「色身(根身)」最為自然而合理。且惠能「身為明鏡臺」實有雙重含義:其一、修行者固然必須以「修心」為首要任務,但亦不應放縱其「根身」而作出「身惡行」及「口惡行」來,佛說「守護根門」即是此意。這因為物質性的「色根之身」是精神性「識心」的依托處,對「識心」是會產生影響力的。後來惠能於《無相頌》中,也有「若悟大乘真懺悔,除邪行正即無罪」,「努力修道莫悠悠,忽然虛度一世休」,又云「色類自有道,離道別覓道」、「若欲見真道,行正即是道」。此間所言「行正」、「一世」、「色類」等都與「根身」有關,修「身」與修「心」不異,亦不應偏廢。所以惠能「身為明鏡臺」句,實暗示不守戒行,則般若靈光亦無從顯發,因此「心平」、「行直」是相輔而不悖。其二、「身為明鏡臺」句,表面雖然重視「守護根門」,但「身」是能照之「心」所依處,猶「明鏡臺」則是能照的「明鏡」之所依處,故「修身」的目的亦不離「修心」,故亦不失「明心見性」的南禪宗旨。 三、不違惠能思想:上文經已論述惠能「心是菩提樹,身為明鏡臺」這半頌,雖與神秀「身為菩提樹,心如明鏡臺」在用詞與句子形式上頗為相類,但其精神含義究竟不相同,所以絕非神秀偈文的重復。至於「心是菩提樹,身為明鏡臺」亦不與惠能思想有所相違。何則?二句之中雖然提及「身」與「心」。「明鏡臺」與「菩提樹」等等名相,但這不過順應神秀原偈而來而加以適當的修訂,以糾正神秀的用詞與思想之失,一如人問及「念阿彌大(陀)佛」,惠能因之而說:「使君東方人,但淨心無罪,西方人心不淨(亦)有愆。迷人願生東方、西方者,所在處,並皆一種…。」非謂在惠能思想中有彌陀義,不過不違自教而順應為說而已。又有人問誦《法華經》,惠能教以「心行轉《法華》,不行《法華》轉;心正轉《法華》,心邪《法華》轉」,是亦非惠能思想中有「轉《法華》」義,不過不違自教而順應為說而已。今「心是菩提樹,身為明鏡臺」亦非指惠能思想中有以「菩提樹」以喻「心」,「明鏡臺」以喻「身」之義,此亦不過不違自教而順應神秀原偈而為說而已,何以得知此二句與惠能思想不相違?如惠能教授「無相戒」,令見自三身佛言:「於自色身,歸依清淨法身佛;於自色身,歸依千百億化身佛;於自色身,歸依當來圓滿報身佛。」此言於自身中,即已圓滿具足菩提三身佛。所謂:「於自色身,見自法性有三身佛。」可見「修身」與「修心」不自偏廢,根本是惠能主旨,故彼偈文與惠能思想實不相違。 復次,惠能於下半偈更能把有異於神秀「漸修」的獨特思想抒表出來。彼云:「明鏡本清淨,何處染塵埃。」偈文是承上文第二句「身為明鏡臺」而來,運用「借喻法」以「明鏡」比喻「識心」;「明鏡」本無「塵埃」以顯神秀「時時勤拂拭」實非必要,藉此暗示能照的「般若正智」(清淨識心),從本以來即是「清淨」,「客塵」煩惱終不能對彼有所虧損,一悟則清淨「般若」當即生起朗照大用,何事凡塵滌蕩殆盡,然後「般若」才能照用。如《壇經》所言:「聞其頓教,不假外修,但於自心,令自本性常起正見,煩惱塵勞眾生,當時盡悟。」足見此偈正與惠能的一貫思想相應,無有相違。故知「明鏡本清淨,何處染塵埃」二句,一方面糾正神秀「時時勤拂拭,莫使有塵埃」的偏差,因為「塵埃」究非「明鏡」之本有,才成「客塵」,才可以「拂拭」得去;若「明鏡」本有「塵埃」,則一切修行,都是徒然。另一方面,此二句又正顯「般若正智」本自澄明,猶如「明鏡」;一切「煩惱」,都是「客塵」,盡皆虛妄不實,究竟無損於「般若智光」。所以,只要「心平」、「行直」,頓悟煩惱非實,當下「般若正智」即能發揮明照大用,體會「本原佛性」,成就「大覺菩提」,所以「時時勤拂拭」亦非必然的修行歷程。所謂「前念迷、即凡夫,後念悟,即佛」。又言「煩惱即是菩提」。此等說法與思想,實亦建基於「明鏡本淨」、「般若正智」本自澄明之上。 (全文完)
|